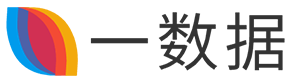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关注
摘要:侗语地名有汉语指称和侗语自名两种存留形式。侗族文化碎片化日益加剧,侗族族群的历史记忆日渐消磨的背景下,自名侗语地名逐渐代之以汉语指称。随着族群记忆名片侗语地名自名的磨蚀,侗族族群面临的不仅仅是语言等文化形态的边缘化,而是族群记忆与认同的危机。
关键词:族群记忆;族群认同;地名
文化全球化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语境中,有些民族还能坚持自身民族的身份,而有些民族则不断被同化,逐渐失忆,甚至失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角逐中,边缘化站位并没有得到大的改观,再加上,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多民族互融体,中华文明自身也存在不同族性文化的博弈。这场文化博弈,没有哪一个少数民族能够缺席,无论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偏安一隅。少众民族的文化弱势日渐凸显,强势文化同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少众少数民族的族群记忆逐渐被剥蚀,族群文化记忆不断碎片化。部分少数民族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危机程度不断加剧。
侗族地名现存汉语指称和侗语自名两种存留形式,随着老龄侗民数量的减少,侗语地名自名知晓率不断降低,进而代之以汉语指称。侗语地名不仅仅为侗族人民居所指称,同时,地名本身也是侗族人民思维习惯、认知方式以及族群迁移历史轨迹的记忆符号。由于汉语指称中侗语地名文化元素的脱落,侗族族群的很多民族文化因子,也随之发生变异,甚至消失。侗族地名的现状凸显出侗族文化的存续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危困的时期。
一、黔东南侗族地名现状
由于侗族族群迁移以及族群与他族之间的融合等原因,侗族地名与侗族族群现有聚居状况并不是一一对应,这在其他民族以及其他区域也同样存在。复旦大学葛剑雄先生认为,苏州被称为姑苏,“姑”没有实在的意义,是越人的发语词,地名以“姑”字开始的,一般都有越人的痕迹。虽然当下的居住人群已经覆盖了区域的原族群,但是作为族群记忆的地名却记忆了族群居住与迁移的历史。
地名辖域的变化,或地名辖域内族群认同的变异,或者地名标签性符号的变更,或者族群外的重新指称,都可能引发某地新命名的产生。对民族地名的深度梳理,既可挖掘被封存起来的历史文化,也可还原族群演变的历程。特别是对于没有民族自身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而言,地名就是其辖域内族群文化的活化石,是了解区域内族群,至少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段族群生存发展的重要史证。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L.R.Pamer)认为:“地名的考察是令人神往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之一,因为地名本身就是词汇的组成部分,并且地名往往能提供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论点。”在新旧文化迅速代谢的当下,很多侗族地名已经被汉译所取代,汉译侗族地名大部分抹掉了地名蕴涵的族群记忆。侗族语言濒临消亡,很多侗语地名已为年轻人淡忘,很有永久消失的危险。深入了解地名的得名、沿革、演变,可以更好地认知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从侗语地名的区域分布来看,侗语地名一是存在于非侗族族群居住区,但从地名来看,该区域内的人口可能是侗族族群的他族同化,还有可能是该区域的侗族人口迁移,居住人群成分复杂,但地名还保留原来的侗语命名;二是侗语地名辖域内居住的族群以侗族人口为主。居住人口的族别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地名的指称有的有历史阶段性的变化,有的仅仅是汉译问题而没有记载族群历史变化文化痕迹。
侗语地名的汉译一般有:
1.专名+“洞、寨”
侗语地名汉译后,存在大量的“专名+洞、寨”的指称现象。通名是“洞”的地名,一般都是专名在前,通名在后。通名是“寨”的有时候专名在前,有时候专名在后。如:
石洞、朗洞、邦洞、摆洞、甘洞、寿洞、寿洞、车寨、票寨、晚寨、平寨、马寨、卡寨、常寨、章寨、新寨、邦寨、口洞、水洞等。
2.“寨、宰”+专名
侗语地名汉译后,通名是“寨”的,有时候通名在前,有时候通名在后。通名在前的侗语地名汉译,有时候通名汉译为“寨”,有时候汉译为“宰”。如:
寨章、寨蒿、宰荡、宰寡、宰麻、宰西、宰东、宰洛、宰官、寨崩、寨高、寨头、寨南、宰拱、宰洋、寨母、宰略、宰劳、宰养、寨欧、寨先、寨霞等。
3.专名+“塘、旦”
侗语部分地名以“塘、旦”作为通名汉译,汉译后通名“塘、旦”一般在后,偶有变音“党”的汉译,“党”作为通名一般在前。如:
龙塘、大塘、党相、党调、定旦、水塘、宝塘、塘旧、党脚、塘洞、党翁、甘塘、小塘、塘流、塘化、塘边、塘沙等。
4.侗语地名其他通名
侗语地名跟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名相似,都有属于本族群的通名命名方式。通名则标志着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分类,记录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各种举措和设施。侗语的通名除了上述几类还有一些其他情况。
多以自然地理指称通名,岑(山)——岑光(剑河县)、岑洞、岑胖等;平(坪)——平岑(剑河县)、平鸠、平友(榕江县);孟(潭)——孟彦(黎平县)、孟伯(锦屏县)等。以辖域状况指称通名较为普遍,寨——寨蒿(榕江县)、宰(寨)白(黎平县)、宰告、栽(寨)麻(榕江县)等。
二、侗语地名及其汉译的对应问题
侗语地名及其汉译虽然是一个侗语地名都必定对应,且仅只对应为一个汉译地名,但是从地名的通名的对应上来看,并不是一个侗语通名必然仅只对应为一个汉译通名。侗语有时一个通名对应为多个汉译通名。侗语专名与汉译对应情况就更为复杂,侗语专名或对应为汉语音译专名,或对应为汉语意译专名,有时候既不是音译,也不是意译,因为无法追溯初始命名的依据,姑且认为其为误译。
1.侗语地名的通名“洞”
甘洞、邦洞、口洞、摆洞等地名的通名“洞”对应为侗语的。一般认为是侗语发语词通名,调查资料显示侗语发语词通名跟汉译语序刚好相反。

有时汉译通名“洞”并没有在侗语地名中有必然的对应。

侗语地名的通名对应为汉译侗语地名“洞”“寨”。如果侗语地名汉译为双音节专名,一般选择为不加通名。如 黄桥。
黄桥。
侗语单音节地名,有时候汉语翻译为单音节侗语地名+汉译通名“洞”。

2.侗语地名的通名“寨”
章寨、新寨、邦寨等汉译侗语地名的通名“寨”,学界一般认为是借自汉语的“寨”,侗语语音为。因为侗语没有汉语舌尖前、后塞擦音、擦音zh\chi\chi和z\c\s,侗语仅有一个舌尖前擦音s与之对应,根据和“寨”的指称和语义关系,是借自汉语“寨”的侗语音变。侗语通名在侗语地名中位置比较固定,一般位于专名的前面,侗语地名汉译后的通名“寨”位置比较游离,有时在前,有时在后。试比较:

侗语地名还较为常见以“宰”命名的情况。侗语地名的通名“宰”不是屠宰的语义,而是村寨的指称。因汉语舌尖前、后塞擦音、擦音zh\chi\chi和z\c\s,侗语都并为舌尖前擦音s,汉译侗语地名“宰”侗语读音为。通名汉译为“宰”的侗语地名,通名“宰”一般位置比较固定于专名的前面。如:


还有宰荡、宰寡、宰西、宰东、宰洛、宰官、宰拱、宰洋、宰略、宰劳、宰养等以“宰”为通名汉译的侗语地名。
三、侗语地名的命名理据
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的“文化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认为:命名活动取决于名称与某种命名活动的因果联系,其所依据并不是名称的意义,而取决于名称的起源和历史,即与名称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影响,而不取决于被命名对象的偶然特征。亦如李如龙先生所言:专名的形成和人们对该地域的最初理解和认识相关,体现着各式各样的“命名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名的“得名之由”。侗语的地名并非随意的约定形成,得名有由,命之有据。
上文例析可见,侗语地名的通名有较为普见通名“洞”“寨、宰”“塘”,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通名“岑”“坪”等。
众所周知,大部分以“洞”为通名汉译的侗语地名,实际上,此地并无洞;而且侗语并不以“洞”的读音指称该地域。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以“洞”为通名汉译的侗语地名,该区域的世居人民一般都是侗族人口。“洞”为通名汉译的侗语地名对应为(寨),无论是意译还是音译,都不可能如此毫无道理。唯有用“洞”为“侗”,即侗族族群聚居的他族指称,来加以解释。也即是,大部分以“洞”为通名的侗语地名,都是侗族人民世居之地,或者曾为他们聚居之所,后因一些原因离开此地,而为他者所居。“洞”的汉语通名实为他称,侗族自称为。
以“寨、宰”汉译的侗语通名,是借用汉语“寨”的读音的自名,还是该区域的人民为先祖移民的后裔,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侗语确实有与汉语“寨”的读音极为相似的村寨命名形式,从侗语地名名词的构词方式上来看,汉语形式凸显的“寨”,词形结构部分已经与汉语构词方式一致,只有少数保留侗语的构词形式。以“宰”为通名汉译的侗语地名的构词形式,即语序,几乎都保存着侗语的构词语序。所以我们不能断定“寨”的通名是否借自汉语的音译通名,作为侗语地名通名来命名。
正如侗语很多地名是依地得名。侗族族群聚居在黔湘桂毗邻的山地,所以地名多以山(岑)来命名,如:岑洞、岑胖、岑友等。这些汉译地名的通名“岑”还有对族群居住地位于山的具体位置指称,如果位于山顶,就以高岑指称;指的是族群居住在山坡上部,位于半山腰,则称之为半岑,山脚称之为定岑,“岑”侗语区的地名读音为“jin(qin)”。居住在山间的平地,由于山区不可能有很大的平坦地带,偶有山间或河边的可供几十上百户人家居住的地方就可以称之为“坪”,然后再加上一个该地物产来命名,从江县县城所在地“丙妹镇”,指称的是该地处在从江河边的坪地上,而且此地树林覆盖,是侗语“坪梅(树)”。
侗语地名的通名“塘、旦”和“党”,《文字集略》早轶,今本是清人马国翰所辑,该书“蜑”作“徒旱反,蛮属。”唐代何超《晋书音义》载:“天门蜑。徒旱反。蛮属,见《文字集略》。或作蜒。”《晋书音义》还提及,时人或将“蜑”写作“蜒”。当时汉字尚未规范,或上下结构,或左右结构,只是偏旁异置,实乃同义。此类情况在当时字书里多有出现。因声旁、偏旁写法相同而发生借用,其用法乃古汉语修辞中的通假。宋代《集韵》“蜒”作“蛮属”解,即与“蜑”互通,义同。唐代以后文人经常“蜑、蜒”互用。宋初,徐铉等人奉诏校订《说文解字》,将“蜑”作为新附字列入字书,解释为“南方夷,从虫,延声”。《太平寰宇记》卷120《黔州》记载:“控临蕃种落:牂牁……蛮蜑,葛獠……俚人、莫猺,白虎。”则宋代黔州(辖境大体为今贵州北部和东部一部分地区)有蛮蜑族群存在。他们直到元代还存在,《元史》卷27《英宗本纪一》载:“丁未,播州蜑蛮的羊笼等来降。”播州(今遵义地区)蜑蛮乃《寰宇记》所记黔州蛮蜑后裔,为元代贵州少数民族。侗语对自称之外其他村寨的侗人也用“旦”来指称。
四、汉译侗语地名的族群失忆
前文侗语地名及命名理据的叙述,可以看出侗语地名是侗族族群对生存境况以及族群与社会、自然关系和族群发展变化的记录符号。侗族文化正在随着侗语族群的减少而逐渐被汉文化同化,再加上各少数民族杂居之间的文化互融,侗族族群文化元素流失加速。婚丧嫁娶等大型族群习俗活动,祭祖、节庆等的族群文化习俗,逐渐淡走,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族群活动中消逝。部分区域仅存的侗族文化样式,也只是徒有其表,没有了侗语作为主要交流工具的文化基础,大部分套用汉语的内容表述,比如侗族情歌、对歌、酒歌等,甚至仅仅保留侗族族群的腔调和韵律,内容几乎使用汉语进行描述。侗语可以说是侗族族群文化记录最为重要的载体,语言的消失,是一个民族文化记忆消逝最为致命的。侗族族群历史、生存经验以及生存环境变迁地承续,没有文字符号作为支撑,完全依赖于侗语的交互传习。当侗语被其他的语言所取代,侗族族群文化残存的碎片,也就只有沉默在学者们搜集整理的文献资料里,以及嵌在侗语地名这个族群文化化石中。
因为没有侗族地名的详细解读,加上族群迁移、古老建筑翻新、原有地理风貌的变化,地名对侗族族群文化的记录也只能是一种摩测。从一些地名的越来越汉语化的替代,可以见出,这些仅存的记录侗族族群历史文化的碎片,也在汉语同化的洪流中风雨飘摇。强势文化来袭并不是任何强势力量的压制,而是强势文化自身吸磁力的强大,以及侗族族群他族文化认同感增强,以及自族族群文化认同危机的表征。族群文化认同的削弱,带来的是族群文化载体的淡走,必然引发族群集体性失语以及失忆。
来源:《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7年09期
作者:龙景科 刘晓洪
选稿:周辰
编辑:袁云
校对:徐省之
审定:徐萍
责任编辑:汪晨云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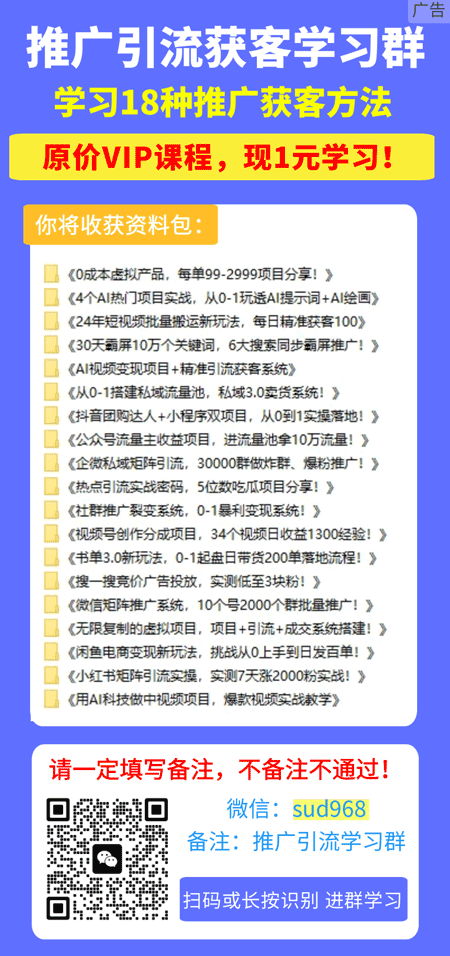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1dat.com/5171.html